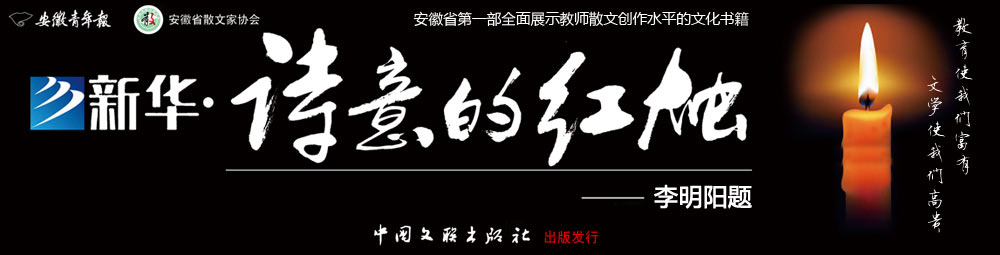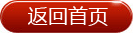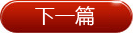星期天,我带着女儿去体育场放风筝,她懒洋洋地不肯奔跑,倒是我似乎童心未泯,把风筝放飞在晴朗的天空。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放风筝是最奢侈的游戏了,现在我手里拿着30元一只的塑料风筝,而当年的风筝是自己动手做的,用的是16开的田字格书法习字本和竹子的骨架,风筝线是棉线,这样的风筝顶多能飞几米高,再高一点,线就绷断了。但那种奔跑、呼吸、放飞的快乐,虽然简单,如今的孩子能体验到吗?
回到小区,偶然看到邻家的小孩在玩玻璃珠,我暗自心惊,似乎从玻璃珠的滚动中看自己单纯、快乐的童年,相信35岁以上的人会有同感。那时,娱乐少得可怜,生活简朴甚至困顿,游戏是最能主宰一个孩子灵魂的东西了。
我慢慢回忆起那时的游戏:伸向知了的竹竿、五彩缤纷的香烟盒和糖纸、抽打后旋转的陀螺、悉心呵护的小蚕、打雪仗、摔泥炮、折纸飞机、挑冰棒棍儿……
用一根粗铁丝扭成的铁钩钩住铁环,在黄泥路与青石巷里,孩子不知疲倦地奔跑。铁环滚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那种声音,直到今天,仍能穿透城市的喧嚣,响彻我的耳边。
“挖沙坑”,好像没有孩子不喜欢沙子的。只要有建筑工地,只要有一堆沙子,总有一群孩子不厌其烦地在那儿挖沙坑。我想,这是受当时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的影响吧,孩子们想把坑挖深一些大一些,可松软的沙子支撑不了,最后塌了,然后挖坑,上面用找来的几根小树枝撑住,再铺上一层纸,最后把沙子慢慢撒上去,努力做得和周围的沙子没有什么两样,一个陷阱就形成了,最紧张刺激的是看谁踩上去,有时是来找孩子的家长,有时是玩耍的同伴,有时是忘了挖坑地点的自己。
女孩子也有自己的游戏,男孩子是不屑于玩的,有时实在没有别的男伴了,也会禁不住诱惑,加入女生的阵营:踢毯子、跳猴皮筋、拾骨头子儿、跳方格、丢手绢、下腰…… “三个字”是追逐的游戏,捕捉的人就要抓住对方,只要说出任意的三个字,就安全了,然后就解放了。如果一时紧张或者说错了,你就要成为那个最孤单的捕手,男孩、女孩疯跑在一起,少小无猜,天真无邪。长大了,再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只在爱情的追逐中,不停地说:“我爱你”。
男孩子比较喜欢军事类游戏,比如抓迷藏、斗鸡、打水漂、打水枪。当夏夜我潜伏在小院的路边,摒住呼吸一动不动,看着搜索的玩伴走过时,感觉自己就是个打伏击战的八路军,心里自豪极了。 我喜欢“丢沙包”,不管是在两边投,还是在中间躲,都需要灵活、机智、果敢。后来,大了,知道了美国棒球,知道了投手和跑垒员,当美国的孩子挥舞着几十、几百美元一根的球棒时,我们正用废布头加上沙子或米粒缝好的沙包游戏。童年,一样的充实而且可爱。现在孩子可以和欧美的孩子同步使用名牌、吃麦当劳、上网、打游戏,他们就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吗?
那些如影附形、如水就岸般承受着快乐的童年游戏,不知道在哪一个早晨或晚上忽然烟消云散,把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赤裸裸地抛散到一片苍茫之中。那些游戏给我们的希望,像是具有魔法的仪式,可以使时间加速或者刹车。在孤独的时候,游戏是陪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的最忠实伙伴。匮乏物质的年代,精神生活却不贪乏,家家的孩子都顺着天性自由生长着,没听说谁因为跌破了头摔折了胳膊去打官司,街坊四邻的孩子好得像一家人。现在,连学校都都不敢组织春游了。看着娇贵的独生子女们坐在网吧里游戏或者结伴到歌厅唱卡拉OK,我不知道应该快乐还是伤感。
与如今五花八门的时髦玩意儿相比,我们童年的游戏显得那么老土、简单,几乎不花一分钱,它们长久地留在记忆中,我理解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折射出时代背景的故土情怀,让我们深深留恋。游戏让我们成熟,以至于长大后我们绝对不敢游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