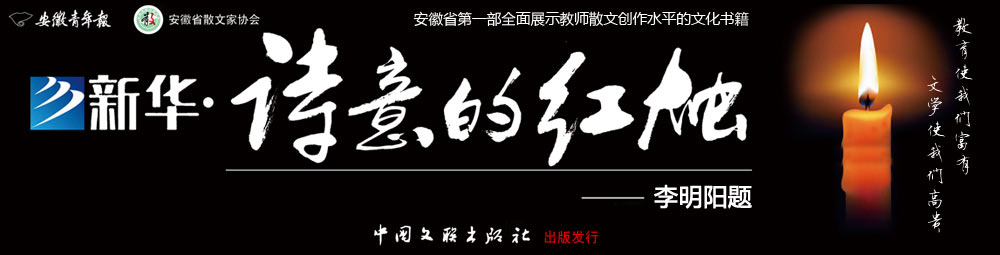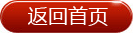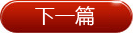妈妈是原四川开县人,从遥远的四川到外陆的安徽这其中有过曲折。外婆是个典型的四川老太太。她老人家一生嫁过两次。第一个是我外公,我没见过,很早就去世了,丢下了外婆、大舅、姨妈和我母亲。可不久外婆改嫁,生了小舅,母亲就停止上学,作姐姐专门待候小舅了。——我很长时间里对小舅不怀好意,他的出世无疑转移了我外婆的注意力,直至母亲辍学。可惜第二个外公我也没机会一睹尊容,具体什么时候死的我也不太清楚,听母亲说这个外公凶得很,而且还有过抽大烟的历史。我猜他当年可能是个地主阔少什么的,不然地主气怎么那么大?
外婆嫁了两次,死了两个丈夫,这在农村是很忌讳的,至少有克夫的嫌疑。所以,从我十一、二岁那年于四川见到她始,就很少见她笑过,一脸的苦相,第一次见她有点害怕。但我也怀疑,是不是这老太太一直对我父亲怀恨在心呢,其实我也说不清当年我父亲在四川上游做买卖时是怎么把我母亲“骗”到手的,但起码是两厢情愿呀。
我去过四川两次。听母亲说,在我十一、二岁那年去之前,我和姐姐就已经去过一次。那时用一担竹筐担着,一头一个,但终因年幼不经事,我毫无印象。第二次去时,我在镇上大姨妈家待的时间长,虽然外婆在乡下大舅家常住,但大舅母这女人太泼辣,我们都烦她。到大舅家得过条河,河中央竖着条船,两条木板左右连着船和岸,过河的只有交钱给船老大,方能过河。春天的时候,河水很急,船板又太窄,我不敢过,只得狼狈的坐在木板上“骑”过去,引得船老大和那些过客的许多“嘲笑”,我记得船老大好像说:“这是哪家的娃娃,要不得!”四川人说“哪”念去声,乍听有唱戏的味道。
外婆的村子后边隐约有山林,我和我表哥上山采过竹笋的,肥大硕嫩的,多的诱人。晚上回去晚了,大舅母就给脸色看,说:“什么伢子野得都不认家喽……”她明里骂的是表哥,可暗地里谁都知道她在说谁。母亲和她这个大嫂关系很紧张,大舅母对她这个小姑子也从没好感,一个女人嫁那么远,一年到头连屁钱都不寄,她很不情愿外婆单单的在她家养老。——我这个大舅母一直以为我母亲很有钱,她哪里知道我家那些年的苦处。外婆那时多躺在床上,她身体本就不好,又没什么照料和营养,一病起来就一蹋糊涂。大概是和她相处的时间不长,对她的初次记忆很空白。对她有较深的印象那是二年后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了。
二年后,外婆决定要到安徽来看看她女儿。母亲大概是担心外婆的身体,就让父亲到芜湖港接她,我父亲对他这个丈母娘是有点敬畏的,他提前二天到了芜湖港。
外婆的到来很“轰动”。一个四川老太太千里迢迢来看女儿,多少是能引得村里其他老太太掉几滴泪的,但多数人还是有点瞧热闹的味道得。初来乍到,外婆讲话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外婆到村里,她不仅是客,而且还是我母亲难得来几次的娘家人的娘,所以来送茶(即待客的茶叶蛋)的人忒多。把这老太太急得说:“要不得,要不得!”“要”也念上声,听起来很有意思。
外婆大约在我们家住了一年的时间。那时我们家还很困难。她身体又常有些小毛病,但很少让父亲请医生来治,说是没那么烦人,喝点草药就行了,其实她是舍不得花那几个钱。她说的草药是那种田野里、池塘边长的大耳朵叶、野席草之类的东西,我和姐姐当年就常和外婆一起去采,采回来洗干净后就煮水喝,我也喝过,外婆说没病也能喝的,这是凉性的。我不知道她这方子是从哪里得知的,我很怀疑它的“凉性”。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天傍晚,我正在家里,忽然村里的四哥跑来,说:“三婶呢(我母亲)?三婶!不好了,你外婆在后山倒了!——三婶呢?”我急忙跑到村外告诉了正在地里的母亲(父亲那时经商在外),她听后边哭边跑向后山,还没到后山,就见到一大帮人向这边走来。外婆正被一个本家哥哥背着,四周是那些腿脚还未洗有点惊魂未定的乡人。——这一幕是我后来对“乡情”最形象的再现。外婆和姐姐在后山放鹅,她是高血压犯了,她把姐姐也给吓哭了。到了家里,几个长辈就好心的唠叨,怪我母亲不该让这么大年纪的人出去“忙”。——其实我母亲哪里让她做这些事,这全是外婆背着母亲做的,我母亲有苦说不出,只得揩眼泪。我很同情我母亲。当晚又有人送鸡蛋什么的来看外婆,第二天,外婆又让我们把东西送回去,还要向人家道谢。我记得外婆是信耶稣的。有一次她和几个族长老太太在屋里准备祷告,要关上门,她问我进不进去,我下意识摇头站到了门外。然后我好奇的从门缝里见到她们极虔诚的跪在地上,两只手按着地,嘴里哼着一种动听的曲子。我不信教,但我后来觉得那仪式绝不会是基督教祷告仪式,此时的宗教可能已经是变了味的,是一个可以负载她们内心苦痛和矛盾的心灵世界。
这老太太不仅能和村里其它老太太处得来,就连我那些年轻嫂嫂、婶娘也乐意和她相处。那时我们还穿手工做的布鞋,就是那种有“千层垫”的鞋。我外婆很会剪这种鞋样,她用纸剪成各种样式的鞋样,然后送给那些小媳妇。那时家境虽大不如今,可有这么个老太太在家还是觉得很热闹的。到她走时,我们都很不舍得。可四川老家来信,说我那泼辣舅母又生了个儿子,要外婆回去照料,很多人都劝她别回去了,省得烦神,但她去意已决。
不想这一去竟是永诀……那年“非典”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外婆突然去世了,听母亲说并非因为“非典”。那时正是“五一”,学校没放假,不让回家。母亲哭着打来电话,说回去是赶不及见外婆最后一面了,爸爸当时寄了几千块钱去,也不想让妈妈那个时候出远门。妈妈说以后只有指望我了,我对妈妈说,以后我一定送您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