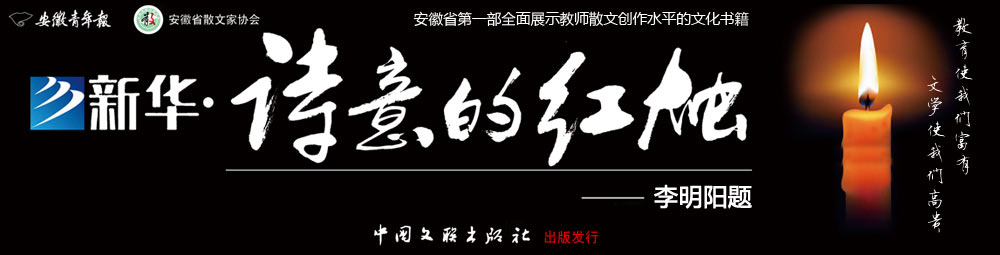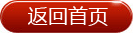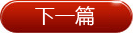题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 因为我对母亲爱得深沉。
母亲1925年出生在一个叫做枣树店的小镇,母亲一生生了四个儿女并养育成人。母亲是1998年离开我们的,可直到今天,我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念着母亲,想念着母亲在时的那个老家。
我的老家在金桥,一排四间草屋,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是我妹夫栽的,每年七月间,石榴花开得如火如荼,待秋天回家时,母亲便踮起脚,从树上摘下几个最大的石榴,带给她在远在城里的孙子。母亲说,待石榴熟透,她还要分一些给邻居的孩子,那些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这些石榴一个夏天了。
老家院里的两棵油桐树是我下放的第一年——1975年栽的,当我不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梧桐树昼夜陪伴着我亲爱的母亲;母亲闲时常抚摸着一天天长大的油桐树,想念着不在身边的儿女。
老家院子里有口压水的井,那是我们多次劝说后,母亲才舍得花钱请人打的。有了这口井,母亲就不用请人挑水吃,不用去塘边洗衣、洗菜了。每逢天旱或雨雪天,母亲还让左邻右舍来此用水。井边有口储水的小水缸,每天早晨母亲总是把水缸装得满满的,于是,她的孙儿、孙女回老家临走时,也学着把缸里装满水,这时,站在一边的母亲脸上便溢满幸福的笑容。
我、妻子、孩子一家三口回家的日子,是母亲最为高兴的日子。母亲最疼爱她最小的孙子,而孙子却难得回去一趟。每当孙子回家的前些天,母亲便忙碌起来,买糖果、买菜,若是冬天,必一遍又一遍地晒棉被。当孙子到家时,母亲就会架起火盆,把她托人从山里买来的炭烧得旺旺的。天没亮,母亲又会赶到集市等着买最大的鲫鱼、最肥的老鸡给她的媳妇和孙子吃,这时候,满街的人都知道,许老太太的孙子回来了。那时孩子小,最多的还是我一个人回家,我一般是早上九、十点钟到家,每次回家,母亲都说她今天不知怎么正好买了好菜。母亲一边做菜,一边与我叙家常。那是怎样幸福的时光、怎样可口的饭菜啊……
母亲知道我冬天易受凉,所以一再嘱咐我冬天要穿得暖和些,尤其下面要暖和,寒从脚下起啊。大约是1986年冬天的一个中午,窗外白雪飘飘,我伏在客厅的桌子上备课,这时有人敲门,开门后,见是一位老家的熟人,他抖抖索索地递给我一个网兜,说是"你妈带给你的"。我打开网兜,解开包裹着的一层层布,里面是一双崭新的棉鞋:黑平绒的面子,白鞋底,一针一线,极其清晰。这是母亲给我做的鞋……是的,母亲做的,我的嗓子一下堵住了……母亲那年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母亲是属牛的。母亲常说:人出生的时辰不同,命也不同,比如属牛吧,一种是吃饱后睡觉的牛;一种是满山找草吃的牛。母亲说她一辈子操心,象找草吃的那种牛。母亲和父亲在街道的小商店工作,商店说是集体办的,其实没什么保障,生意好的时候,有人来检查、来收费;生意不好的时候,找谁也不管,所以母亲一直盼望我们好好读书,以后好有个正式工作。商店有三间门面,木板门、泥柜台,靠墙一排货架,上面摆满杂货。集镇上的小店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天亮卖货,夜晚关门。母亲和父亲每天大约在天明前两小时就起床了,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边扫地、抹桌子、生煤炉、烧水。把家里打扫好后,又一道去商店打扫卫生、整理商品,开门营业。我爱人在机关和校园里长大,属于晚睡晚起的人,刚到我家时怎么也不适应,常问我,你家人怎么天没亮就不睡觉了呢?
母亲晚上也去店里。柜台上摆一盏被母亲擦得极明亮的煤油灯,灯下,母亲嗤啦嗤拉的纳着鞋底,有一笔无一笔地卖着货。我上小学的时候,常跪着长条板凳爬在柜台上,在母亲抚爱的目光下和沙沙的纳鞋声中写字、做功课,大约到晚上九点钟的样子跟着母亲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说话,有时母亲问我,你长大跟谁过,娶不娶老婆。我说,我不要,我跟妈过。那时的我,回答是认真的……有时,月光如洗,蛙声如潮,我和母亲谁也不说话,我是在专心地看着地上随我和母亲移动的身影,而母亲在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放假的时候,我白天把作业做完,晚上就不到母亲那去了,而是到一个叫做农产品交易所的地方听大鼓书,可每听到关键处,母亲便喊着我的乳名唤我回家。母亲的呼唤是亲切的,她让我记忆终生,诗人但丁曾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母亲个子不高,但母亲是个极坚强的人,面对困难、面对打击,她从不叹息、从不低头,我极少,不,应当是从没有见过母亲流过泪。我的祖籍在河南商丘,听先人说,自祖父辈以上七代行医,经年累月,家藏医书数卷,先人中还有一人曾救活一位垂死的年轻孕妇,被当地誉为有起死回生之术。可惜至祖父辈时,祖父的一个兄弟为鸦片所染,卖去祖传医书,以致家道中落。我的祖父是由河南逃荒到安徽一个叫金桥的地方。那是个小集镇,有谁在这样灰色的小镇上生活过吗,单门独户,举目无亲……。父亲是个认真而文弱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作为孩子的我们,那时从心底感到孤独和无助,在那时,惟有母亲能保护我们,她不低头、不掉泪,站得稳、走得正,她坚信日子会好起来的。我很喜欢听一首叫做"好大一棵树"的歌,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便想起我坚强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有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回忆起来,只朦胧记得外婆和母亲在家里对面坐着叙家常的样子,外公的模样我是一点也不记得了。舅舅一生无儿女,后来我大哥过继给了舅舅。可舅舅、舅妈去世早,大哥文革中也死于肾炎……,想起来,母亲娘家可谓伤心至极。但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未提及这些。今日想来,年轻的母亲觉得孩子尚不省事,讲这些孩子也不懂;中年时,母亲整天想的是几个孩子成家立业的事,更无暇谈及;待到母亲年迈与孩子是聚少离多,或许担心在短暂的团聚中谈及这些伤了儿女们的心,所以把这些伤心的事一直放在心底。法国一位哲人说,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雪,漫天皆白,地上积雪盈尺,清晨,我得知母亲垂危,于是踉踉跄跄往母亲住处赶。这时,大脑恍恍惚惚,一片空白,只觉得路上人很少,出租车几乎没有,大地静得出奇,白雪让人头昏目眩,我没有思想、没有悲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我努力在想,我在哪,我去哪?我怎么想起了1984年,那也是好大的一场雪,积雪没膝呀,可那是我的孩子出生的日子呀……难道……我的亲人生与死的日子……都和大雪有关吗……惶惑中,有一辆的士在我面前缓缓停下,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似乎说看我有急事,就停下让我上车……,我怎么啦,我在梦中?是的,我做过这样的梦,母亲去世了,我大哭……猝然哭醒,原来大梦一场,母亲并未去世!悲去喜来,我的心怦怦地跳,于是赶紧在星期天回家看望母亲。
但这次…… ,这次……母亲真的去世了!母亲永远地走了……
母亲走了,我不用牵挂她了,不用牵挂她在雨里,不用牵挂她在风中,不再牵挂她生病,也不再牵挂她节日的孤独了。我没有妈妈了,没有人像母亲那样管我了,可我的妈在哪啊,我的家在哪!当我出差在外,身处日暮黄昏的旷野,看到炊烟缕缕升起时,我听到母亲悠长的呼唤;当我外出归来,回到城市,万家灯火扑面而来时,我听到了母亲悠长的呼唤。
母亲去世后,我朝思暮想,但一直也未梦见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后一个多月的一天夜里,我突然梦见母亲或者说母亲来看我了。那是在金桥老家的屋子里,母亲和衣而睡,衣服极整洁,面部极清爽,神情也极安详。我不相信是真的,我担心这是梦,但抬头看却真是金桥老家呀,房子中央还是横着一根挂毛巾的铁丝,用手一摸铁丝上的毛巾还湿漉漉的呢。我赶忙呼唤母亲,哭诉我们以为她去世了,诉说我们对她彻骨的思念…… 大梦醒来,万籁俱静,拧开灯,时针指在两点,我睡意全无,心中百感交集,惆怅万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有能力使母亲过得好些的时候,母亲却走了,当我真正懂得孝心母亲的时候,母亲却走了……我对得起母亲吗,天知、地知、母知、我知,然而,慈母已逝,茫茫天地间,谁能告诉我!
我不知道是否有天人感应之说,反正母亲出殡的那天,天突然放晴,一路上,青松翠柏,一路上,白雪皑皑。太阳透过树林,赤橙黄绿,毫光万道,似在为母亲送行。我心中感慨万千:"慈母西去心欲摧,白雪漫天泪满衣。可叹一别成千古,而今只盼梦中归。芳草萋萋年年碧,思母情长夜夜啼。最怜老父依闾望,风急天高孤雁飞"。我把我的这首诗,把我滴血的心、长流的泪,把我那无穷无尽的思念,跪献于母亲的坟前,愿她在遥远的天国——幸福、平安。
我和我的老师
年龄逐渐大了,便喜欢回忆过去的事,尤其回忆那些曾经引领、帮助、关心过自己的人,老师,便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在金桥小学读书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合院式的小学建在小山坡上,这所大人看似一般的小学,在孩子的眼里却是无比的阔大,学校里的老师更是非同寻常。郭崇武是我的语文老师,细条个,长方脸,大眼睛,一副军人身上才有的机警和干练劲,人也耿直。他的字写得尤其好,大概学的是柳体,很清秀。除了字写得好外,同学们还传说他身上有些功夫,据说两三个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有这样的老师,顿觉安全了许多。郭老师兼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六年级时我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戴三条杠的臂章,与郭老师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郭老师对我很好,教我做少先队的工作,他也很信任我,放假了,他要回城里了,就让我代看他家的门。我们的教导主任姓童,童什么?记不清了,但模样记得清楚,个子不高,宽额头,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是一条的,头发稀疏但梳的讲究,眼睛很有神,象谁呢,比较起来有点像萨马兰奇。踢球是童主任拿手好戏,学生爱看。童主任不是在地上踢球,学校院子不大,又没有现在的草坪,踢不起来。他踢的是儿童拍的小皮球,你看好,站稳了,运足气,把球轻轻抛起了,待球下落时,右腿后摆,脚尖绷直,飞起一脚,好,脚尖直击小球,遭到重击的小球笔直地向空中射去,越来越小……在学生的一片欢呼声中,童主任双手叉腰仰望天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欢呼之后的我们顿觉浑身轻松,随着上课的铃声,叽叽喳喳跑向教室。学校的校长姓卫,叫卫道仓,黑皮肤,小个头,个子虽然不高,可全校老师没有不听他的,服他,为什么,人家实干、苦干、有威信。我们学生一般跟他接触不上,但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时我已经六年级了,随着马路那边中学红卫兵上街游行,我们小学的课也不上了,停课闹革命了,回家了。不久,学校又把高年级一部分同学叫回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回到学校闹革命的几个同学,晚上挤睡在院子里用课桌拼接的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分吃着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西红柿。这时,卫校长走过来,小声地说,你们白天对我的批判不行,没有力量,你们要讲得狠一些,这样才能通得过,你们几个晚上一定要想一想。吃柿子带来的兴致很快就没有了,大家翻来覆去想如何使批判有力的事,想到最后,终于想到卫校长曾批评我们下河洗澡的事,就拿这件事批判他吧。于是第二天会上我们说,卫校长咒骂我们革命小将,说我们不该私自下河洗澡。这时卫校长抬头望望我们,似乎觉得还没力,我们一急,就把家长骂我们的话用上了,他还说下河洗澡淹死了,还不如汽车压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到。这句话似乎有力,因为大家都不吱声了。晚上在院子里睡觉时,卫校长又慢慢走过来,寒暄两句后说:同学们,我记得我可是没讲过汽车压死比河里淹死好的话,你们再想一想。后来好像我们也没再想了,只是觉得话说过头了,对不起老校长。小学毕业后,我没能升上初中,在家呆着。记得有天傍晚,卫校长来到我家门口,站着与母亲叙话,大意说我学习很好,学校原先还打算发展我入团的,升不了学是因为有人写信反映我父亲历史复杂,让我母亲不要责怪我……。母亲听着,一直不说话,怔怔地看着站在一旁的我,眼眶里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上不了中学,只有在家了。后来说是可以上一所农中,我就去看了那所农中。山坡上盖有四间房子,孤零零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没看到老师,于是我也就死心了。上初中是三四年后的事了,其间,我就跟着被下放的父亲学农活,拾粪、砍草、贩卖米糠、开荒种菜,还拉过大锯。拉大锯能挣几个辛苦钱,但活太重,一般人干不下来。自己除了有点累也倒没什么感觉,可母亲难过得不行,跟我二哥说,太小了,会伤筋骨的,不能再干了,还是找找人让他上学吧。二哥找了一个教过他书叫做“二陶”的老师,陶老师说,上初一年龄大了些,读初二吧。于是我就上了金桥小学附近的金桥中学。毕竟初一的书没读过,上初二底气不足,尤其怕提问。教数学的老师是位女的,叫江正岚,瘦瘦的、高高的、黑黑的,戴一副镜片有点黄的眼镜,很少笑,就是笑,笑意也就是在唇边一带而过的那种。江老师数学思维极其清晰,课讲得干净,按农村话说,如劈干柴一般,对学生很严厉,批评人也如劈干柴一般。前边的课我都没学过,但她不管,专找你提问。最怕的是她把题目在黑板上出好以后找学生上去做。每当这时,她的目光缓缓地扫过全班,全班同学也缓缓地低下头去。“李明阳”,我头脑一炸,然后是一片空白,也不知怎样走上讲台、怎样下来的,只是事后下决心要学好数学。除课堂学之外,跟我二哥学,他是高中的老三届学生,功底好,后来数学成绩也就慢慢上来了,一次全校数学竞赛还得了个三等奖,为此江老师还让我到她家吃了顿饭。但数学我还是怕学,时至今日做梦,往往是数学考试的试题做不出来,以致急出一身冷汗来。语文学习就不一样了,语文老师叫汪淑仙,也是位女老师,白皮肤,略微有点胖,戴副红边的眼镜,一团和气的样子,课上课下经常听到她爽朗的极富感染力的的笑声。每周一次作文课是我最高兴的时光。她从厚厚的一摞作文本中抽出我的作文,高声地朗读,细细评论,然后再让同学评论,这时,同学便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汪老师的作业批改也十分认真,她会在她认为写的好的段落画上红圈圈,写上许多鼓励性的话语,也会在眉批中指出你的不足。我读高中时换了个语文老师,新语文老师原先在合肥那边工作,叫赵一新。毕竟是合肥去的老师,做派跟当地老师不一样。一身黑色的中山装,皮鞋也擦得干净,笔挺的。赵老师个头不高,宽额头,瘦下巴,上唇好像有短短的胡须,不苟言笑,很有点像鲁迅的样子。第一天上课,走上台来,也不自我介绍,只是拿起粉板擦在讲台边缘磕了磕,转身将黑板上没擦干净的地方擦了个干干净净,捡了支尚未用过的粉笔,干咳两声,抬起臂,沙沙地在黑板中间写下要讲课文的名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呀!就这几个字,把学生给彻底镇住了,没见过写得这么好的字,刚劲有力,棱角分明。接下来是讲课,条分缕析,细致入微,有板有眼,再现了鲁迅先生文章的论战风格,学生觉得如饮甘露,如沐春风。下课铃响了,大家方从课文中醒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以示崇敬,赵老师在大家敬佩的目光中飘然而去,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的反应。到后来,赵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我也当了班长,他放手把班里的工作让我做,使我得到学习以外的锻炼,当然这是后话。赵老师现在合肥,我自己忙于工作和生计,很少看他,前不久,在合肥的几个同学把赵老师夫妇请到一起,共进晚餐,共叙师生相处的日子,其乐融融。那天,我给赵老师送了一副自撰自写的条幅:“斗转星移四十年,丘壑也已化桑田。更喜千流归大海,师生谈笑忆从前。”那晚,赵老师喝了好几杯酒,闲聊时话不多,一如既往让夫人讲。看得出是十分的高兴。
我是由下放知青考入安徽师范大学的,属于习惯上称作“七七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后十年未进行高考,七七年的首次高考,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进入高校。广大学子带着振兴国家的使命感,如饥似渴地学习。高校的教师也从“牛鬼蛇神”的阴霾中走到阳光下,走上阔别多年的讲台一展身手。在我就读的中文系,那时张涤华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是著名语言学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成果涉及目录学、词典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众多领域,大家尊称他为张涤老。张涤老属于我们为之骄傲和仰慕的老前辈,那时年事已高,不上课了,偶尔开讲座,大部分时间是闭门著书立说。我因为与张涤老的儿子张劲秋是同班同学,有时应邀去他家玩。老先生清癯,和蔼,穿着布纽扣的中式服装,温文尔雅。每次去都见他坐在藤椅上写东西,桌子上放的是让我们感到很深奥的线装书。我们这些学生去他家,认识不认识的,他都站起来点点头以示欢迎。我们上学期间,中国女排很火,每场球举国关注。那时电视机很少见,大部分人都是围着一台收音机,收听著名播音员宋世雄的现场解说,宋世雄的解说也确实好,干净利落,语言流畅,声音具有穿透力。但张涤老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更想看画面,看比赛实况。于是,张涤老便让家人把所有小板凳集中起来,排成两排,好让我们都能坐着看比赛……。孔子曰:“逝者如斯”,去年已是张涤老诞辰一百周年了,我作为学生参加了纪念活动,有感于先生的高风亮节,书写了一幅“智者虚怀如水静,高人清品与山齐”的条幅以为纪念。我的大学老师中还有位叫余恕诚的老师,讲唐宋文学,对唐宋诗词的研究造诣颇深。余老师属于不故意显山露水的那种人,讲课时脸上始终带着谦逊的微笑,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如杜甫《春夜喜雨》所赞美的“好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如春雨般的话语来拨动你心灵深处的感情之弦。他的诗词分析有极鲜明的节奏感,一如宋代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所写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由“黑云翻墨”到大雨滂沱,再到风吹云散,最终进入“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的水天一色的澄明境界,一堂课,便是一次感情上跌宕起伏的历程。余老师待人宽厚,因为是肥西老乡,更因为他的平易近人,与他渐渐熟悉起来。老师话语不多,作为学生的我亦如此,每次到他家后,路上准备好的几句话不多久就讲完了,然后便是静坐了。余老师的老伴来自家乡的农村,但余老师夫妇相处得极好,记得每当讲到老伴晚上端热水让他泡脚时,老师脸上便弥漫无限的温馨。在我的印象中,余老师属于不会经营人际关系的人,本色处人,书法大师启功先生说“立身苦被浮名累,处世无如本色难”。可见本色处人是很不容易的。余老师一直当教师,自己也乐此不疲,后来听说他获得全国教学名师的殊誉,并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可想而知凭的是真才实学,也应了一句老话:“养成大拙方知巧 学到如愚乃是贤”。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赵庆元老师算是年轻的了,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中的元明清部分,有激情,口才极好,讲课十分生动。北方人性格,豪饮,喜交朋友,与学生称兄道弟。我是通过同学黄元访认识他的,记得有一个冬夜,外面下着雪,在他低矮而暖和的屋子里席床而坐,一个鱼头、一斤酒,三个人,没有酒杯,就倒在一个把缸里轮换着喝,边喝边海阔天空地吹牛,那酒喝得——真是——不亦乐乎。可惜庆元老师英年早逝,真可谓:“一生坎坷路,满腹元明清”。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位老师,正是这些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老师的教育、引领、帮助、关心,才使自己健康成长。年少时体会不深,取得一点成绩,私下里总以为是自己一身的本事,经历的世事多了,方才真正明白一个人从小到大,成人成才,都饱含许多老师的心血和汗水。还是那首歌唱得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