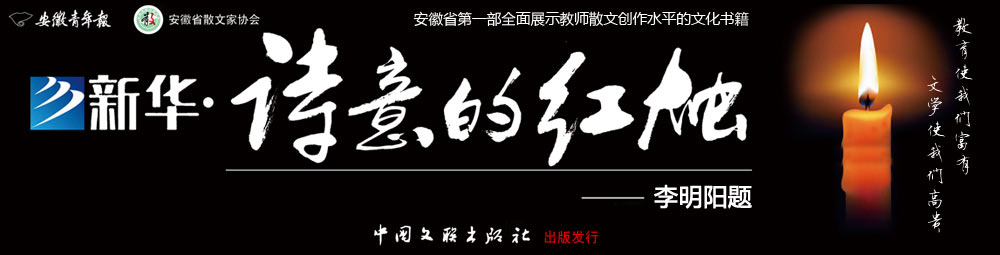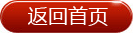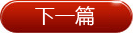佝偻着干瘦的身子,拄着根竹拐杖,每走完三四十米就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剧烈地咳嗽着。这是我脑子里外婆生前的身影。
我的记忆里,外婆一生曾建立了三个家。
外公、外婆、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组成了外婆的第一个家庭。这本应该是个幸福的五口之家。可在那个饿死人的年月里命运之神并没有格外开恩。两个年幼的舅舅相继饿死,而接受不了丧子之痛的外公也走失并长眠于离家二十里地的众兴集附近。“你姥爷的尸骨到今也不知道埋在了哪里,每年上坟就只能在三叉路口烧些纸钱了。”母亲常常和我说起她小时候的事,“家里只剩下我和你姥姥了。那时候虽然每天都能在野地里挖到吃的,可我还是黄嘴白牙的每天只知道哭。哭得你姥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我带到了这里。”母亲说的“这里”指的是我的老家,也是外婆改嫁后建立第二个家的地方。
婆也常常对我说起她以前的事。但说到她第一个家的那段时光,外婆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姥爷不是死早了,我说不定也会当上干部的。”外婆所说的“干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外婆经常给我讲当年她是多么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一个又一个的妇女工作任务的。后来在整理外婆的遗物时,我又发现了一些她珍藏的诸如红五星,红袖章之类的东西。看着这些小东西我又仿佛看到了外婆在那个激情岁月里为革命为新生活热情工作的身影。同时我也暗暗庆幸那段时光留在外婆记忆里的并不是无边的悲痛。
改嫁后的外婆又生育了四女两男,加上我的母亲和继外公前房留下的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外婆第二个家里的人口竟有十三人。在责任田到户之前,我的父母只养活我们四口之家日子尚过的很贫困,家里常在青黄不接时节断了口粮,这很难让我想象出外婆在养活十一个孩子时是怎样艰难度日的。
两次组建家庭,外婆生育了九个孩子,共抚养了十三个(加我先前饿死的两个舅舅)孩子。因此我一直认为晚年的外婆之所以身子骨那么干瘦,像被掏空了似的,就是因为多子的缘故。试想想在那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生下孩子并一个个抚养成人,身体是很难不被拖垮的。
继外公终究没有把小舅舅的婚事完成就撒手离世了。为了小舅舅的婚事,外婆花光了微薄的积蓄最后还是在母亲他们众姊妹的资助下才把事情做好的。可到最后外婆就只能在一间原来作为走道的小屋子里生活了,外婆把她最后的三间土屋也给了小舅。
最后小屋实在没有办法居住了,外婆就请我父亲他们帮忙在旁边盖起了一间只有二十几平方米的土屋子。可这屋子遇到阴雨天地就变得又湿又滑,冬天屋里也是湿冷湿冷的。恶劣的居住环境更加重了外婆的哮喘病,此后每年冬天外婆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打着点滴度过的。后来实在喘的很了,外婆就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种粉状的白药,吃了能很有效地暂时镇住剧烈的咳嗽。但别人告诫她那药有毒,要尽量少吃。可服用了一段时间的外婆,每天都要大剂量的用药才能见效。这时外婆胸透的结果是肺泡已经大量纤维化了。
在外婆的这最后的家里,我唯一感到新奇的就是一块用红布遮盖的神位。那里供奉的不是观音也并非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里供奉的据说是黄大仙(黄鼠狼)的神位。这神位是一位相头(乡间的土女巫)亲戚在继外公死后替外婆请的守护神。而外婆什么都给了两个舅舅,只有这神位随着她到处搬迁。每日早晚外婆必定要做的课业就是焚香祷告,为自己更为自己的孩子们。
外婆虽然一生被孩子操劳,但对所有的晚辈来说她都是慈祥的,尤其对我更格外看得重些。虽然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和外婆大吵大闹,但无论她们怎样吵闹,我都是可以不受影响地到外婆家去,继续享受“乖这乖那”的优待,我的整个童年也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也正因如此,我对外婆也格外眷念,外出求学时,外地工作时,只要我回老家,无论时间多么紧,我都要到外婆的小土屋里陪她说说话,帮她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
几年前,舅舅们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孤零零的外婆固执地住在小土屋里照应着三家的空房子。前年秋天,有了积蓄的小舅盖起了楼房,外婆的小土屋也被拆除让出了地基,这时外婆才住进了小舅的楼房里。
住进了宽敞干燥的房子,外婆那年冬天就很少打点滴了,药也服用的少了。但我却常常看到外婆佝偻着干瘦的身子,拄着根竹拐杖,每走完三四十米就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剧烈地咳嗽着……
谁能想到没有了自己的家的外婆竟没有能等到新年春天的到来!
今天,外婆的坟地已经淹没在荒草之中了。站在满目荒凉的坟地旁,我想这里才是真正属于外婆自己的“家”。
回想外婆坎坷的一生,我不禁潸然泪下。愿外婆在天堂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