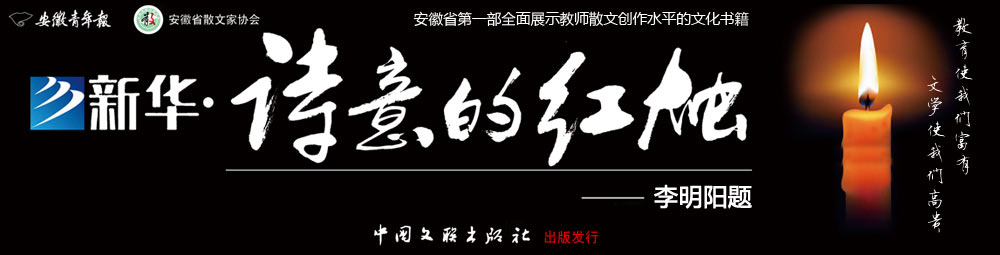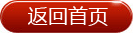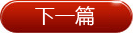从深秋到隆冬季节,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如果你来到我们太湖县的山区,你就会看到一幅奇观:空旷的稻场上或宽阔向阳的山坡上,成片成片的是用直径约1米多的巨型圆竹匾晾晒的豆粑,豆粑做工精良,质地微白中稍稍偏黄,是用上等刀功切成的均匀的细长的片状,在充足的阳光下晒上两三天,就干了,就可以放进竹筐、木桶或纸箱中储存几个月了。无论炒、煮、焖、蒸,都是特别诱人的一道营养佳肴,更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日思夜念的美食。
用竹匾晾晒的豆粑在阳光下泛着美玉的光泽,十几户人家的“杰作”在稻场或山坡上排列成整齐的队伍,绵延一里多路,蔚为壮观。
豆粑的制作是很有讲究的。先把绿豆、蚕豆、豌豆、红豆、黄豆等各种豆类淘洗干净,磨碎、去壳,和洗净的大米、芝麻一起用大木桶装上大半桶,放入满满一桶水,浸泡一天一夜。豆子、大米和芝麻喝饱了水,浸透了,肚子鼓鼓胀胀的,就可以合水放进石磨碾磨成浆。
白嫩白嫩的浆从两扇石磨之间慢慢渗出来,渐渐地汇成了“瀑布”流泄到下面的大木盆里。
磨浆是慢工出细活。每次用勺子舀大半勺料倒入磨眼,等磨盘转两三圈再舀大半勺料倒入。不可急躁,快了浆液粗砺,味道差。如此下来,待全部料磨成浆,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料多时需耗时一天。
烫豆粑,当地叫唱(读作:“chang”)豆粑,是农户一年一度的大事、喜事。一家有喜,户户帮忙。日含山,鸟投林,唱豆粑开始了。唱豆粑这活儿不怕人多。这一边,正在清场子,抬几张大方桌,另放几条长凳,上面备好早已洗净晾干的圆形大竹匾,其它家具一律靠边、出门,几大捆松毛(干枯的松树叶子)搬到厨房边;那一边,挪几条短凳或大木椅,放两个大木盆正在兑浆。将磨出来的浆液兑上水,搅拌均匀,要求不稀不稠,稀了,唱不成张(整张),稠了,唱出来的厚薄不匀。兑浆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大多由主妇主持。兑浆的说一声“好了”,掌勺的系上大围裙上岗了。先将两口大铁锅和要用的杂件检查一遍,齐了便发令“烧(生)火!”约一分钟,他将手背靠近大铁锅探一探,立马知道火候,如果正好,他就大喊一声“上浆了”,(火工答一声“知道了”,声音更响亮)随即拿起一块长五六寸的大肥肉,“兹啦”一声在热锅上轻快地摩擦、游走几圈,放下肉,又拿起能装一斤多浆液的勺子舀起一浅勺米浆沿锅口一寸许处环绕一圈,把米浆均匀地倾注到热锅里,闪电似的放下勺又拿起一个大蚌壳,将尚呈液态的米浆抹开,抹得联成一体,厚薄一致,放下蚌壳,盖上锅盖即转战到第二口锅旁。第二口锅的工序完毕,第一锅应该刚刚烫好,就双手轻轻掀起,翻个身烫一下另一面即双手擎起甩在身旁倒扣的筲箕上。这道工序劳动量大,很辛苦,热锅高温,豆粑蒸气,烟熏火燎;难度也极大,要精细,要敏捷,要连贯,稍欠功夫不是不成形就是生熟不均,不是生熟不均就是烧糊烧黑,一边自己操作,还要大声(人多嘈杂)指挥烧火的、兑浆的……经验老到又年轻力壮的师傅完成这道工序则如行云流水,绵延起伏、丝丝入扣,游刃有余。成品则厚薄一致、色调一致,可谓增一分则太厚,减一分则太薄,深一分则太黄,浅一分则太白,甚至张张大小一致,香味则浓郁而醇和。当然火工也是老手,巧妙配合,火大了不行小了不行,动作慢了不行快了不行,不是烤,不是熬,不是煎,而是恰到好处——烫,其玄妙就在一个“烫”字!
然后呢,放在筲箕上经过初冷的豆粑要转移反铺到已经准备好的竹匾里进行再冷却,十来岁的小孩子最喜欢作这“转移”工作,他们争抢着、欢叫着。反铺到竹匾里要一张张掀开再铺平,十几分钟后经内行检查再一张一张折叠成匀整的条形卷子,搬运到靠里的房间,切成细长的片状。这道工序虽男女不限,但多由细心爱美的少妇少女操作,她们往往要先检查卷子,热了则粘连,冷了则太硬,切起来费力又难完形,卷子不匀整要重折,否则切出来容易走样变形。你看,三五个箩筐、三五个刀手排列开,三五把闪亮的快刀,三五人一齐动作,优雅整齐,响声轻微匀和,如舞如乐,如诗如歌。
第一张豆粑出锅,就有人笑嘻嘻来“尝新”,烫了一小半,主人就吩咐家里孩子(也有邻童)挨家挨户送热豆粑(这是农村风俗),说是给老人尝尝,这时内行来换班的,评论“指挥”的、揩油沾光的,甚至比赛谁吃得多的、围观起哄的,陆续登场,兑浆者、掌勺者、烧火者、搬运者、折叠者、送礼者、操刀者……从厅堂到厨房到内房一律灯火通明,里里外外都是人,处处欢声笑语,不乏打情骂俏者,也间有粗言俚语,但整个工序环环相扣,井然有序。
这样熬个通宵,三五斗米的豆粑就唱完了,切豆粑的人也把豆粑切成了均匀的细长的片状,装满了几个箩筐。
太阳出来了,一担担豆粑就上了山坡,去了稻场。一年的福气和好运也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