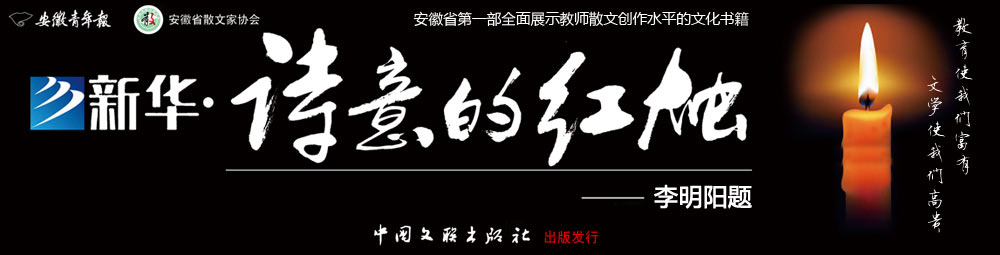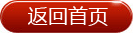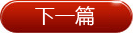在一个略带寒意的春晨,我驱车前往山皱褶中的一所小学,看望在那里当“孩子王”的高中同学。一路颠簸,一路猜想着这个同学当下的生存状态。
同学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叫春花。据说她出生时,正在田里劳动的父亲,看到一株开得正欢的迎春花,眼睛倏地一亮,信口掐出这个名字。其实,春花打小就长得水灵,上高中时已是凹凸有致玉树临风的美人坯子。考大学因几分之差,名落孙山,尔后到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本校的一名老师。最近又听说那位老师在山洪爆发时,因抢救学生,丢下娇妻爱女,撤手而去。
春花是个代课教师,没有正式身份,靠区区300、400元的微薄收入,维持家人的生计,生活无疑是清贫的,甚至捉襟见肘。
我想帮她一把,劝她加盟我的公司,过一过城里人的生活。再说,待遇也比当代课教师要丰厚得多呢。
老同学来访,且开着一辆锃亮的宝马轿车,煞是招摇,宁静的校园一下子喧嚣起来,师生们象见到神奇的怪物,“呼啦啦”围了过来。有个胖胖的女同学自告奋勇去寻春花老师,片刻功夫,她乐颠颠地拿来一串叮当响的钥匙给我,说:春花老师正在上课,叫你先上屋里坐一会儿。
屋子是两间矮小的平房,红砖青瓦,墙面没有粉刷,裸露着,“原生态”。屋子很洁净,没啥摆设,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更没有什么现代化电器。墙角上放了个竹制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有文学名著,有教学辅导用书,还有小学生的作业本,杂且乱。
吸引人眼球的是简易书桌上竟放着一把黄色的小花,似跳动的火焰,给昏暗的屋子抹上一点亮色,透出一缕春的气息。
我神情为之一振。哦,迎春花。一种极普通的花,山上、田野里,俯拾即是。它并不娇贵,更不张扬,匍匐在地,用柔软之躯阅尽风霜冰雪,在料峭的寒风中,用鹅黄色花瓣展示它的美丽容颜和生命张力,是开在春天里最早的一种花。
我原先的担忧一扫而光,仿佛看到花的主人倔强的目光,触摸到她生命的顽强和高贵。我默然地带上门,悄悄地将钥匙放在窗台上。
驾车回城的路上,我神情有点沮丧和恍惚,眼前跳动的总是那团火焰般的迎春花。
[page]初中那些事儿[/page]
我上初中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处在拨乱反正、社会转型的时期。
上初中头两年是文革尾声,当时不重视学习,很看重劳动,劳动是件光荣的事。
春天学校布置我们打秧草,每个学生都定量,我们就起早摸黑地割草,争先恐后地送到学校。于是,学校操场堆起了一座座绿山。然后,农民伯伯就将绿山运走,放在田里沤肥。我们做得很认真,每个同学都能完成指标,还将草洗得干干净净,生怕有点泥土,挨老师批评。
秋天,稻子熟了。“喜看稻菽千重浪”,挺美的。学校又将我们组织起来,到乡里割稻支农。我们从家里带着洗涮用品出发了,驻地离家仅有几华里,但晚上我们都吃住在生产队,连续几天不回家。尽管割稻又苦又累,一趟稻割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一张小脸都红扑扑的,汗像蚯蚓般在脸颊上爬,但大家兴致都很高,稻田里的鸟儿都被我们的笑声惊得扑棱棱乱飞。
农忙季节,学校要放一个礼拜的农假。我在那时学会了栽秧。栽秧是个技术活,行距、株距难把握,栽得既直又快,难度系数不亚于“空中翻腾两周半”。我一天能栽八分田,顶一个劳动力,连老农父亲都夸我秧栽得不赖呢。
我们也很顽皮。知了一叫,我们就像一群鸭子往水里钻。但老师管束甚严。他用自己的私章,沾着红彤彤的印泥,盖在学生的腿上。下塘洗澡了,红标记没了,老师就叫你去谈话,不留情面地剋你,甚至将这事捅到家长那里,我们就不敢越“池塘”一步。
我最怕老师家访。当下通讯发达,老师找家长举手之劳,一个电话就能搞定。那时,老师就要迈开双腿,一步一步地去丈量路程。有一次,我正在玩耍,本村一个同学叫道:“吴老师来了!”吓得我赶紧躲了起来。吴老师是城里人,星期天不常回家,喜欢走村入户家访。他一边帮大人们干农活,一边拉呱。学生们的“天机”是在不知不觉的拉呱中泄露了。全班学生家住哪个村,家中几口人,家境如何,他都了然于胸。撒谎逃学,打架滋事,也都瞒不过他那双法眼。他说话慢条斯理,从未见到他大发雷霆,但学生都怵他,敬畏他。我们都是在他目光的注视下慢慢长大。
要说学习,更得益于初中最后那个学期。本来1977年初中学习就可划上句号,忽然上面来了新精神,延迟一学期毕业。这半年真学了不少东西,超过前三年知识储备的总和,收获颇丰。
晚上,我们到学校去上自习。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集体上晚自习,同学们兴高采烈,挑灯夜战。可那灯不是电灯,是煤油灯。虽然是带罩的,但早上起来洗脸,用毛巾一挖鼻孔,漆黑一片。天热蚊子多,我们就将脚伸进装满水的桶里,既凉快又不怕蚊子叮。最要命的是没有学习资料,谁要弄来一道题,全班同学一哄而上,抢着做。做完了,就互对答案,其乐融融。
中考时间在7月份,我是光着脚上考场的。顶烈日,冒酷暑,来回要走十几里地。好像没有什么压力,考完了就算了。不像现在的学生,一遇到考试就紧张、烦躁,甚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等待考试结果却是难熬的。一个多月后,知道考上了中专。那时一流成绩才能上中专。上了中专就意味着鲤鱼跳农门,穿皮鞋,住洋房,捧铁饭碗。
我考上中专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四邻八乡,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鞭炮声也不绝于耳。
我三年半的初中生活也在鞭炮的袅袅烟雾中与我挥手惜别。
今天回味起来,初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恐怕也就是这些“鳞爪碎片”。33年没有抹去的记忆,自有它的道理。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爱因斯坦说,当我们把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全部忘掉之后,剩下来的才是素质。诚哉斯言!